演出市場
演出市場
- 烏蘭牧騎來到北京航天城慰問演出,這份
- 2018山東省首屆旅游商品博覽會將在泰安舉
- 余干《今日黃港》自籌經(jīng)費開展“歡樂鄉(xiāng)
- 人民大會堂元旦期間演出看看那場你喜歡
- 平陰縣文廣新局:組織開展基層綜合性文
- 民間劇團演出現(xiàn)場座無虛席 越劇在紹興有
- 國內(nèi)實景演出數(shù)不勝數(shù),但是知名的不多
- 演出行業(yè)莫忽視小城青年
- 24部新創(chuàng)大戲集中亮相山東文化藝術(shù)節(jié)
- 菏澤首屆激光水幕電影兼璀璨花燈兼國際
聯(lián)系我們
郵 箱:yewu@ningxiu.com
手 機:178-528-25688
網(wǎng) 址:http://ittalk.org.cn
微 信:jinanyanyi
地 址:濟南市歷下區(qū)經(jīng)十路黃金時代
演出市場
從茶資到票價:京劇演出市場化的興起
作者:寧秀文化
發(fā)布時間:2020-03-12 08:10
作者簡介:曹南山,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專業(yè)博士研究生,浙江傳媒學院戲劇影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晚清民國戲劇史。
基金項目: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課題“近代京劇演出形態(tài)與劇場形制演變關(guān)系研究”(編號:18NDJC155YB)的研究成果;浙江省教育廳一般科研項目“基于近代劇場形制演變下的京劇演出研究”(編號:Y201738338)的研究成果。
伶人以演戲為謀生之手段,除宮廷和家樂演劇之外的戲劇班社演出必然要向觀眾收取一定的費用,這便是戲價。清代梨園中曾用“茶資”指稱戲價,清末民初“票價”逐漸取代“茶資”成為戲價的代名詞。從茶資到票價的轉(zhuǎn)變,反映出清末民初京劇演出生態(tài)的重要變化。
在近代梨園文獻中,“戲價”一詞較票價內(nèi)容更為豐富,既指觀眾到戲園看戲支付的費用,又指戲園一天演出的收入,偶爾也用于指稱名伶的包銀。相比而言,票價一詞更直接準確地體現(xiàn)了觀眾看戲所需的費用。票價的出現(xiàn)是演劇活動高度商業(yè)化的產(chǎn)物,昭示著京劇演出市場化的興起,清末民初票價的演變和設(shè)定彰顯了演劇市場化的特征。
一、從茶資到票價的演變
戲劇演出的商業(yè)屬性由來已久。據(jù)元初散曲《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記載,“莊家”進入勾欄“要了二百錢放過咱”。古代朝鮮保存下來的元代文獻《樸事通諺解》中有入勾欄看雜技,有“諸般唱詞”,入場交了“五個錢”的記載。①這“二百錢”“五個錢”是目前我們所知最早的戲價。此外,演出過程中伶人還可能會再向觀眾討賞錢。無論是戲價還是賞錢,都是戲劇演出過程中伶人技藝與觀眾欣賞之間自由交換的產(chǎn)物。
戲劇演出從元代的勾欄瓦舍到清代茶園演出之間出現(xiàn)了一個歷史斷層。這期間,目前我們尚不清楚明代民間娛樂化的戲劇演出形態(tài)究竟如何,但我們通過清代民間演劇,大致可以推測此前鄉(xiāng)村演劇的情形:
在前清時,每一本戲不過南錢八吊(合京錢八十吊。此戲價系全班伶人得之因喜慶或酬神而演戲之主人翁者,非觀者所納之資。蓋吾鄉(xiāng)戲,多在廟中演唱,完全公開,觀者不費一文錢也。)②
這種私人包辦的演劇活動和堂會演出相似,都是由一家主人付給戲班演出費用,普通觀眾則不必付錢。
清初,戲園和酒館戲劇演出尚不具備市場化特征。乾隆三十一年(1766)《長洲縣志》記載:“蘇城戲園……不過商家會館借以宴客也。”③顧祿《清嘉錄》言:“蓋金閶戲園,不下十余處,居人有宴會,皆入戲園,為待客之便,擊牲烹鮮,賓朋滿座。”④顧祿是清道咸年間蘇州文人,可見彼時戲園演劇尚承載著宴飲功能,而非純粹營業(yè)性戲劇演出場所。而酒樓酒館演劇更是宴客飲酒的點綴,是極少數(shù)縉紳才享有的娛樂方式。伶人的演戲收入是戲目的固有價格和主人給的賞錢。演劇作為一種商業(yè)活動,具有商業(yè)特征,伶人可以通過演劇獲得一定收入,演劇可以兌換成金錢,但遠沒有達到市場化的程度。大約在同治末年,上海戲園逐漸取消了宴飲功能,據(jù)李興銳同治九年(1870)農(nóng)歷十月初六日的日記記載:“趙小山邀至東門外慶芳園觀劇,又至名慶館飲酒……”⑤由此可見,此時觀劇和飲酒的場所已分離,不然作者當無必要觀劇后重新找酒館飲酒。演劇成為戲園的主要功能,《申報》中則較為詳細地記載了上海戲館這一功能的演變過程:
上海戲館昉于同治初年,其時各省匪蹤未凈,商賈之輻湊于是者,幾于寸地黃金。富紳巨商起居華侈,酬應揮霍,每當列筵顧曲之際,招妓侑觴,雖千金之賞亦不吝惜。以故戲園賣座輒包一席,擺酒請客二席三席,以至于廳樓全包者有之,其價并酒筵由戲館包辦,動須每席二三十元。自江浙楚皖漸次肅清,旅人星散,游宴之舉稍殺于前。而洋場華靡之風日甚一日,酒館林立,如金陵之新新樓、復新園,天津之慶興樓,本幫之泰和館等家,無不樓房高敞,門宇軒昂,椅桌器具杯盤什物,式式精美,凡宴客者皆于酒樓而不于戲園。自后戲座惟清茶一碗、果點數(shù)碟,而其價亦漸減于前。若包一房不過六元,包一桌則四元而已,單客點座每位洋八角,出局之妓亦止一元,如是者有五六年。⑥
演劇場所由戲園酒館到茶園的演變突出體現(xiàn)了演劇商業(yè)化的特征。這種轉(zhuǎn)變顯示,戲劇演出不再附屬于宴飲娛樂,而逐漸成為一種獨立的娛樂形式。演劇的商業(yè)性開始突顯,戲劇具有了獨立的經(jīng)濟價值,人們要專門為看戲付出一定的費用。戲劇的商業(yè)屬性日漸成為演劇活動的主導因素,茶園營業(yè)性戲劇演出開始興起。
茶資作為早期茶園營業(yè)性演出收取的戲價形式,有著歷史的特殊性。茶園的來歷雖有多種說法,但乾隆年間已有茶園演劇的記載,當可確信無疑。⑦茶資取代戲價作為觀眾看戲所付銀錢的稱謂,與清代禁止旗人出入戲園有關(guān)。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禁八旗官員遨游歌場戲館”⑧,但旗人子弟入戲園看戲卻未禁止,及至乾隆元年(1736),禮科掌印給事中德山上奏折“為請禁旗人入園看戲”,乾隆帝批示:“著交與步軍統(tǒng)領(lǐng)并八旗都統(tǒng)查照舊例禁止。”所謂舊例主要還是針對八旗官員而言,并未全面禁止旗人入園看戲。⑨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諭令禁止旗人出入戲園酒館,同年又禁在京有需次人員出入戲園酒館。禁令頒布之后,約一年時間京城戲園封閉,不聞管弦之盛。“嗣以皇太后萬壽召集名優(yōu),猶須預先排演御制之戲曲,乃稍稍弛禁。舊日戲園遂改頭換面,易其市招為茶園,以遵功令。”⑩
戲園(戲館)改名茶園之后,因為對當局禁令依然有所忌憚,便不稱戲價而稱茶資,后來逐漸習焉不察,成為一種習慣。而票價的出現(xiàn)要到光緒中期,劉菊禪記載:“皮簧班在同治年間。四大徽班在平沿演之時,無所為票價。僅收茶資數(shù)十文而已,至光緒中葉。伶工戲份,漸漸加高,方有票價之說。”(11)待到光緒后期,票價逐漸取代茶資,“一九○五年前后,北京各茶園已逐漸由‘茶資’改為‘票價’,可是天津各茶園仍沿用著由來已久的‘茶資’舊制。”(12)事實上,作為一種稱呼習慣,茶資代指票價依然為部分觀眾和從業(yè)者所使用,但即便是稱茶資,使用者實際所指的已經(jīng)不是早年的茶水錢了,而是特指看戲的費用。直到20世紀30年代,這種稱謂現(xiàn)象才完全改變,茶資遂專指戲園和劇場中飲茶消費所需負擔的錢數(shù),票價成為普遍指稱戲價的名詞。
無論是茶資還是票價,都彰顯出演劇商業(yè)化特征。戲劇演出的獨立經(jīng)濟價值得到承認,演劇也成為戲班和戲園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而從茶資到票價,雖看似僅僅是一個稱謂的不同,而實際上卻體現(xiàn)了承載演劇活動的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庚子年(1900)前,北京城內(nèi)的各戲班是按期在各大茶園輪轉(zhuǎn)演出,戲班的演出水平雖有高下之分,但因為所演周期固定,并不能完全決定茶園的營業(yè)狀況。換言之,水平高者如三慶班的演出具有較高的上座率,而它在一個茶園的演出時間只有四天,初一至初四是在三慶園,初五至初八便要到廣德樓,如此便導致,當時八大戲園之間始終保持著勢均力敵的平衡狀態(tài),即便園主讓戲班每天更換新的演出劇目,其盈利的空間也極為有限,待該戲班轉(zhuǎn)到其他戲園時,同樣的劇目依然具有號召力。但庚子年之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
此時北京戲場已與前不同,從前各戲園是各班輪流演唱,喚作活轉(zhuǎn)兒,如今改了一班永占一園,喚作呆轉(zhuǎn)兒。那大柵欄廣德樓、三慶園、慶和園、慶樂園,門框胡同同樂軒,糧食店中和園都被義和拳燒掉,只剩肉市廣和樓,是福壽班占了。鮮魚口一家雜耍館子天樂園,是玉成班占了。譚鑫培本是同慶班,今已改福慶班,占了西珠市口天和館。寶勝和占了天壽堂,義順和占了孝順胡同燕喜堂。(13)
庚子年時局的動蕩對戲劇生態(tài)產(chǎn)生的影響巨大,同樣是庚子年之后,北京戲園的票價不再保持統(tǒng)一,各班各園開始各自設(shè)定演出票價?!肚灏揞愨n》記載:“光緒庚子以前,戲園定價,每座售錢百三十文。自經(jīng)拳匪之變后,蠲除舊例,各自為謀,各園戲價始參差不一矣。”(14)戲班輪轉(zhuǎn)演出慣例的改變,將茶園與戲班的利益密切捆綁在一起。戲班在市場上的號召力直接決定了茶園的盈利程度。為此,戲班和茶園都在爭奪觀眾方面費盡心思。而隨著演出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市場成為京劇演出的主導力量。為了爭取演出有更好的上座率,更大程度的占領(lǐng)市場,盡可能地實現(xiàn)演出利益的最大化,戲園經(jīng)營者在戲園的硬件方面(如茶園的設(shè)施)和軟件方面(如茶園的內(nèi)部管理)等多方面紛紛采取措施。以往的按茶碗收取茶資的經(jīng)營方式已然無法滿足京劇演出的實際需求,為了更多的從演出中獲利,票價便成為調(diào)節(jié)演出市場中供需平衡的主要手段。
而伴隨著上海新舞臺的建立,新式劇場逐漸涌現(xiàn),在新式劇場中用茶資指稱戲價已經(jīng)顯得不合時宜,票價自然要順理成章的代替茶資,成為劇場經(jīng)營中更契合時代潮流的趨勢。此外,經(jīng)營新式劇場所需的費用要比之前的茶園大得多,倘若不能在票價上有所增加,新式劇場將難以為繼。但票價如若定得太高,營業(yè)情況也會受影響。1914年楊小樓創(chuàng)建的第一舞臺便是典型的案例。第一舞臺最終營業(yè)慘淡,其原因當然比較復雜,但時人也清醒的指出:“半因京中戲價素廉,而彼處礙于零星使費特煩,售價若不加增,即無以因?qū)﹄s費,分等定價,較諸舊式茶園之售價,驟增三倍且強,此營業(yè)上失敗之最大原因。”(15)在京劇演出逐漸走向市場化的大背景下,票價高低的設(shè)定成為考驗戲園經(jīng)營者把握市場能力的重要方面。
從茶資到票價的轉(zhuǎn)變過程同樣是戲園文明進化的過程,這個過程體現(xiàn)了演劇市場化對戲園經(jīng)營產(chǎn)生的影響。起初,由茶園中案目按茶碗收取茶資,此后,戲價從茶資中分離出來,戲價和茶錢分別明文寫在戲單上:
“用新式鉛字戲單,戲價茶錢,都明定規(guī)則,排印在戲單上,令人一望而知。大約正東戲價,銅子二十余枚,茶資兩枚;邊廂減半,樓座加半。”(16)
當戲價從茶資中分離出來時,實際上對茶園來說也是增加了一項收入。盡管當票價獨立出來之后,茶資只占茶園經(jīng)營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事實上這一部分收入也不容忽視,畢竟很多人還專門借此營生。
茶園中的戲劇演出獲得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這就必然導致戲班和茶園經(jīng)營者為了謀求更高的收入,要千方百計地吸引更多的觀眾前來看戲。茶園作為開放的營業(yè)場所,南來北往的人員眾多,單靠數(shù)人頭收取戲價,難免會遺漏。更何況,故意躲避收取戲價的也大有人在。這一點,時人已有指出:“不賣票便無限制,難免擁擠,隨意出入,無從檢查,往往有漏收戲價的。”(17)改良這一弊病的方式當然是在戲園門口設(shè)立一柜臺,欲進戲園看戲喝茶,首先得買票。宣統(tǒng)二年(1909),時人已有“及至一進園門,先上柜房兒買票”之說,可見當時北京城買票之舉已屬平常。
在上海,1908年新舞臺建立,暫時廢除了案目制,改為售票制,只是時間很短,后又恢復了案目的作用。彼時,北京新建之文明茶園,有意改良舊式茶園的計劃,比如,文明茶園售堂客包廂之票,票面明確寫明戲價,另有茶水錢銅元四十枚,特別注明“并無別項花費”。然而具體實施時,卻又時常與舊式茶園無異。僅就買票入場而言,茶園既對外售票,自然是有座提供給看戲人,但事實并非如此,有觀眾抱怨說:“在下想著:已經(jīng)付了戲錢,必定有人接待嘍。設(shè)或人要上滿了,柜上絕不接錢呀。呵呵!真沒料著,我們一進堂門,敢情已竟高朋滿座啦(這個滿字,須得重讀)。”(18)
這位在京的觀眾,在文明茶園受到了非常不文明的待遇,買了票,卻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坐,回去之后十分惱怒,這才給報紙寫了批評文明茶園的文章。除了進門買票無座之外,文明茶園也不按票價收錢,這當然有礙“文明”之名。于是有觀眾向報館投訴:
愛國報館臺鑒:文明茶園售堂客包廂之票,上書戲價之外,有茶水錢銅元四十枚,并無別項花費字樣。其所以定限制者,甚符文明之事實矣。乃本月二十六日,內(nèi)子在東樓倒關(guān)二等包廂請客,看座人索去茶水錢四十枚之外,又索茶葉錢四枚,又索伙計零錢十枚,謂票上所書之四十枚,系照數(shù)交柜,看座人之生活,則賴向客座乞討。該園既系如此,大可將“并無別項花費”六字注銷,何苦自相矛盾?但圖文明之外表,抑系看座人既領(lǐng)工錢,又復私行羅掘,局外人不得而知。但覺于文明二字,不甚相符耳。素仰貴報箴規(guī)商界,匡助文明。(19)
文明茶園之所以顯得不文明,其根源就在于:當演劇市場化逐漸興起后,戲園經(jīng)營者尚不能以新的管理和經(jīng)營思路來應對。從柜房到看座人(案目),他們只想著能拿到更多的錢。而之所以他們能這樣做,與當時尚不規(guī)范的票價設(shè)定很有關(guān)系。
二、演出市場化與票價的設(shè)定
茶園所收之茶資和元代瓦舍勾欄的“五個錢”“二百錢”有相似之處,都是按人頭交錢,在茶園則是按茶碗收費,有一碗即收一茶資。這和之前民間酬神演劇和堂會演劇以及酒館點戲就有了巨大差別。此前戲班演戲的戲價是固定的,但凡有人出錢請戲班演戲,無論觀看人數(shù)多少,戲價是不變的。而茶園演劇中的收入是按人數(shù)(茶碗數(shù))來計算,則進茶園的人數(shù)越多,茶園和戲班的收入相應越多。彼時,茶園和戲班分立,茶園邀請戲班入園演出,無論其分賬的比例如何,則總收入越多,戲班和戲園收入自然隨之增加。
園主為了增加收益,開始想辦法招攬更多客人。而戲班為了能更多搭園演出,也在內(nèi)部按叫座能力分給伶人包銀或戲份。茶園演劇的商業(yè)化程度越來越高,叫座成為考量伶人藝術(shù)水準和演出劇目的最重要指標,而票價的漲跌又反映出伶人在觀眾中的叫座能力。
隨著京津滬等地茶園的興盛,茶園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這種競爭局面引發(fā)的直接結(jié)果就是對具有高叫座能力的名伶和劇目的選擇和爭奪。名伶成為茶園營業(yè)盈利的重要保障,各園主逐漸爭相邀角,以增加茶園演出的上座率。名伶在觀眾中的號召力,突出體現(xiàn)在戲園演出的收入方面。以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天仙、丹桂、桂仙和春仙茶園為例。是年,汪笑儂、陳俊廷和程永龍三人由桂仙改班加入天仙,桂仙生意一落千丈,“即漸與諸園相形見絀”,因此園主特委派開口跳蔣寶珍赴京邀角。蔣邀到名伶劉永春等來滬演出,于是“桂仙生涯陡好”:
初五晚桂仙部新到角色劉永春、小福才、王玉芳第一日登臺,座客甚形擁擠,后至者幾無立足處。是晚并系漲價,得如是之盛,可見得人則昌,誠非虛語,而較諸前此,則又不僅利市三倍矣。(20)
但不久,“劉永春在桂仙,頗覺郁郁不得志”,后離開桂仙。桂仙生意再次滑落。及至幾番周折,桂仙請到譚鑫培前來助陣演出,生意之興隆頓時前所未有。但等到譚鑫培離開桂仙,改班天仙,桂仙的生意再次跌落。到中秋節(jié)前一天,桂仙經(jīng)營收入僅有十六元多。但名伶朱素云中秋節(jié)來園客串三天,又再次使桂仙起死回生。僅三天時間,就賣出看資一千多元。當時報載:
至桂仙,小叫天未到時,正廳只賣一角五分,虧折之巨,頗為岌岌。幸小叫天登臺,三十二日賣洋萬余元,始資彌補。迨小叫天去后,仍跌為二角,至中秋前一日,僅賣洋十六元有零。十五日朱素云上臺賣至二百八十九元,看客大半為雨所阻,未能賣足,談者咸以為憾,然此二百數(shù)十元,實皆為素云來也。設(shè)使素云不登臺,十五雖系節(jié)日,亦不過賣至四五十元,倘欲再多,恐亦未必。(21)
由此可見,當時桂仙茶園的生意起落顯然是由是否有名伶加入左右。而此時除丹桂茶園角色齊整,本身有夏月潤、潘月樵等名伶外,又演新戲,營業(yè)保持穩(wěn)定外,其他茶園均以外請名伶為號召。當時上海戲園主要的天仙、丹桂、桂仙和春仙茶園于中秋演戲收入分別如下:
春仙:五百數(shù)十元;
丹桂:三百數(shù)十元;
桂仙:二百八十九元;
天仙:一百數(shù)十元;(22)
之所以有此差距,因為春仙有名角孫菊仙,桂仙有朱素云,丹桂本身有名角,天仙賣座最差,因為沒有與之相力敵的名角。
而同年在上海的名角譚鑫培、孫菊仙和朱素云,三人的叫座能力又不相同,這從搭班茶園的演出收入一目了然:
譚鑫培在桂仙演出《打棍出箱》,夜戲,賣洋六百數(shù)十元;(23)
孫菊仙在天仙演出《御碑亭》,中秋節(jié),賣洋五百十九元;(24)
孫菊仙在春仙演出《舉鼎觀畫》,禮拜六夜戲,賣洋四百數(shù)十元;(25)
朱素云在桂仙演出《白門樓》,禮拜天夜戲,賣洋三百九十元;(26)
三位名伶叫座能力差異之明顯,恰恰表現(xiàn)出觀眾對他們表演水平的認可程度。同為內(nèi)廷供奉,但演出市場卻殘酷地給他們標出了不同價碼。通常名伶的藝術(shù)水準是通過內(nèi)行對其舞臺表演水平來判斷的,但隨著商業(yè)化逐漸在演劇活動中起主導作用,名伶所享有的名聲便由內(nèi)外行結(jié)合其表演水平和叫座能力共同決定。正是基于此種綜合考量,戲園經(jīng)營者給名伶開出了不同的包銀。而名伶演出的票價差異也反映出演出市場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
伶人成名之后被稱為“角”,但“角”有大小之分。民國七年(1918年)周劍云曾將名角分為超等角色(如譚鑫培)、優(yōu)等角色(如楊小樓、梅蘭芳)、頭等角色(如尚和玉、蓋叫天、王又宸、王鳳卿、時慧寶等)、二等角色(如毛韻珂、賈壁云、黃潤卿、趙君玉、白玉昆、楊瑞亭等)、中等角色(如王靈珠、三麻子、林樹森、麒麟童等)、四等角色(如趙如泉、常春恒、小孟七、小達子等)。(27)周劍云對當時享譽京劇界的名角等級的劃分,同時體現(xiàn)出他們在市場上不同的叫座能力。而正是這叫座能力不同,導致他們之間的收入也存在很大差異。為了支付超等和優(yōu)等角色高昂的演出費用,并借機盈利,園主必須在演出票價上有所體現(xiàn)。譚鑫培和孫菊仙等名伶的演劇經(jīng)歷便充分反映出這一現(xiàn)象:
譚叫天南來獻技。……此數(shù)日中。新舞臺之戲價倍于平昔。如臺坐售兩元一票。花樓售十元一間。站臺售一元五角一票。推而至極各售一元。遲到則加坐。仍須小費。以坐容三千號直劇場。每夕八時。必宣告客滿。(28)
民國四年(1915年)農(nóng)歷四月二十三日,天津南市廣益大街廣和樓的日場演出票價為包廂一元,而夜場由于有名角孫菊仙的演出,票價賣到六元多。(29)
現(xiàn)今留存的戲單為我們比較名角演出的票價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試比較兩張民國九年的演出戲單所載的票價:
民國九年三月初一日禮拜一夜戲,梅蘭芳王鳳卿在上海天蟾舞臺演出
票價:特別花樓大洋三元,特等包廂二元五角,優(yōu)等包廂二元五角,特別官廳大洋二元,頭等包廂大洋二元,頭等正廳大洋一元,三層花樓大洋半元,三層特等四角八十,三層頭等三角六十,仆票大洋三角
民國九年三月廿三禮拜二,亦舞臺夜戲
價目:月樓六角,特別包廂五角,特別官廳五角,頭等包廂四角,頭等正廳二角,二等正廳角半,仆票一角
演出劇目:貴俊卿、張國斌、張月亭《全本三國志》
比較以上兩張戲單,演出時間是同一年同一月,都在上海,天蟾舞臺的最高票價是亦舞臺的五倍,普通座位的票價也比亦舞臺高得多。究其原因,固然有天蟾舞臺的硬件要比亦舞臺好,但最主要原因還是梅蘭芳和王鳳卿的出演保證了如此的高票價依然可以有很好的上座率。而這三元的票價相比平常的演出已經(jīng)高得出奇,然而還并不是此番梅蘭芳南下演出的最高票價,待到梅蘭芳臨別演出時,園主又根據(jù)市場行情,臨時將票價增加到四元。如此高昂的票價卻一點不擔心上座率不滿,足見園主對梅蘭芳演出市場的精準把握。初步統(tǒng)計,梅蘭芳此番南下演出四十天,天蟾舞臺的收入是14萬多元,盈利有7萬多元,這筆收入當然是靠票價收取的。(30)
而到民國十一年(1922年),已躋身超等角色的梅蘭芳演出票價已經(jīng)前所未有,試看下面兩張戲單所載票價的比較:
民國十一年(壬戌)五月初六禮拜四夜戲,天蟾舞臺
價目:優(yōu)等花樓大洋四元,最優(yōu)等官廳三元五角,特別包廂大洋三元,特別官廳大洋三元,頭等正廳一元五角,二等正廳大洋一元,三層花樓大洋七角,三層特等大洋五角,三層頭等大洋三角,仆票大洋三角
演出劇目:梅蘭芳、姚玉芙(牡丹亭.春香鬧學)(倒第三),王鳳卿《戰(zhàn)樊城》《長亭會》(雙出壓軸),楊小樓、梅蘭芳《新長坂坡》(大軸)
民國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禮拜四夜戲,亦舞臺,
價目:月樓一元,特別官廳八角,特別包廂八角,頭等正廳四角,二等正廳二角
演出劇目:白牡丹《千金一笑》(倒三),王又宸《李陵碑》(壓軸),綠牡丹、楊瑞亭、王又宸、白牡丹等《新八臘廟》(大軸)
這兩張是同一年上海兩家舞臺演出戲單,上面清楚地記載著演出的票價。梅蘭芳在天蟾演出的最高票價是大洋四元,而亦舞臺最高票價是一元,而通過演出時間的比較,我們還可以看到,亦舞臺這張戲單是新年正月十三演出的戲單,通常來說,這是京劇演出的黃金時間,票價要比平常的日子貴。換言之,這是戲單所載的演出陣容所能設(shè)定的最高票價。因此,他們平時演出的票價與梅蘭芳相比,差距實際上更大。
以上所載戲單的票價信息充分反映出名角出演對票價設(shè)定的影響。正是在高度商業(yè)化的演劇環(huán)境下,票價成為調(diào)節(jié)戲園承載觀眾數(shù)量的重要手段。超等角色的演出票價倘若與普通名角相一致,勢必造成大量觀眾涌入戲園,這不僅超出了戲園所能承受的觀眾容量,也不能實現(xiàn)園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從票價的設(shè)定可以看出園主對演出市場的掌控能力,同時演出票價的不同也反映出觀眾對京劇演出的選擇傾向。票價最直接地體現(xiàn)出演劇市場化興起的特征。
之所以說從茶資到票價的轉(zhuǎn)變是京劇演出市場化興起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因為在這個轉(zhuǎn)變過程中市場的選擇已經(jīng)逐漸對演劇活動起著重要的調(diào)控作用,伴隨著這個過程,京劇的演出機制發(fā)生重大變化,戲園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而票價的演變,最直接地反映出市場對京劇演出產(chǎn)生的影響。當市場開始成為演劇活動的主導力量時,戲園之間的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自由競爭是演劇市場化興起最典型的特征。名角演出只是戲園爭奪觀眾贏得市場的一種手段,此外,新戲(時事新戲、古裝新戲)和連臺本戲都成為一時之選,京劇演出市場空前繁榮,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京劇演出市場蓬勃發(fā)展,到30年代,京劇藝術(shù)達到其最繁榮的時期。這不僅體現(xiàn)在演出市場方面,更表現(xiàn)在京劇藝術(shù)本體的長足發(fā)展。而京劇藝術(shù)鼎盛時期的到來,正是在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下,京劇從業(yè)人員,包括名伶、文人編劇、舞臺美術(shù)和燈光制作人員等后臺人員以及眾多戲園經(jīng)營者不斷嘗試創(chuàng)新、日夜摸索,在謀生的天然秉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業(yè)沖動中,京劇藝術(shù)得以充分發(fā)展。
演劇市場化興起之后,資本和市場成為影響京劇發(fā)展最重要的外在因素。資本家和戲園經(jīng)營者最大程度追逐利益的本性逐漸注入到京劇發(fā)展的體制中,從而對京劇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在這場市場化的演出大潮中,金錢的誘惑太過強大,伶人和京劇從業(yè)人員當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資本和市場的操控通過演出的收入內(nèi)化成伶人的自覺追求,從而徹底喚醒了伶人的商業(yè)意識,其中牽涉到京劇發(fā)展的方方面面,這容待專文論述。概言之,在這種市場化的競爭氛圍中,有些創(chuàng)新和探索已經(jīng)溢出了京劇藝術(shù)所能涵蓋的邊界,成為曇花一現(xiàn)的雜耍和另類藝術(shù)形式。然而,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和教訓都彌足珍貴,因為他們既觸摸到了京劇藝術(shù)發(fā)展的邊界,又擴展了京劇藝術(shù)所能承載的容量。而這些寶貴的歷史財富,正是在演劇市場化興起之后才得以取得。
注釋:
①參看楊棟:《元曲研究失落的兩部珍貴域外文獻——對〈樸事通諺解〉與〈老乞大諺解〉的幾點認識》,《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卷第4期。
②周公旦:《鄂西之民間戲劇》,《半月戲劇》第1卷第7期,1938年。
③轉(zhuǎn)引自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139頁。
④顧祿:《清嘉錄》卷七,傅謹主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八),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63頁。
⑤李興銳:《李興銳日記》,《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柒),第398頁。
⑥《論戲價不宜太減》,《申報》,1885年10月7日。
⑦參考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149頁。
⑧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0頁。
⑨丁淑梅:《清代禁毀戲曲史料編年》,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1—82頁。
⑩詩樵:《京華菊部瑣記》,周劍云:《鞠部叢刊.梨園掌故》),交通圖書館,1918年,第7頁。
(11)劉菊禪:《譚鑫培全集》,上海戲報社,1940年,第14頁。
(12)李相心:《天津戲園的變遷》,《中國戲曲志天津資料匯編》(第一輯),中國戲曲志天津卷編輯部,1984年,第61頁。
(13)陳墨香:《觀劇生活素描》,《劇學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
(14)徐珂:《清稗類鈔》(第十一冊),中華書局,1984年,第5044頁。
(15)天傭:《楊小樓傳》,《十日戲劇》,第1卷第22期,1938年。
(16)《請看文明戲園》,《順天時報》,1907年3月2日第5版,《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伍),第333頁。
(17)《記改良北京市(七)》,《順天時報》1907年9月21日第5版,《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伍),第442頁。
(18)冷眼人:《觀劇難》,《正宗愛國報》第567期第5版,1909年,《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六),第165頁。
(19)董竹蓀:《來函》,《正宗愛國報》第567期第4版,1908年,《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六),第144頁。
(20)《桂仙生涯陡好》,《消閑報》,1901年4月25日第350號,《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續(xù)編》(四),第21頁。
(21)《菊部要志.記各園生意大略》,《世界繁華報》,1901年9月29日第85號,《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續(xù)編》(四),第144頁。
(22)《談劇》,《寓言報》,1901年9月29日,《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六),第201頁。
(23)《梨園雜志》,《寓言報》,1901年8月27日,《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六),第201頁。
(24)《菊部要志.記孫菊仙登臺》,《世界繁華報》,1901年9月28日第175號,《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續(xù)編》(四),第145頁。
(25)《梨園雜錄》,《寓言報》,1901年9月30日,《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六),第201頁。
(26)《梨園雜錄》,《寓言報》,1901年9月30日,《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六),第201頁。
(27)劍云:《平包銀議》,周劍云:《鞠部叢刊.劇學論壇》,交通圖書館,1918年,第16—17頁。
(28)楊塵因:《譚叫天南來十日評》,《春雨梨花館叢刊一集.劇評》,民權(quán)出版社部,1917年,第1—2頁。
(29)李相心:《老戲單》,《中國戲曲志天津資料匯編》(第一輯),中國戲曲志天津卷編輯部,1984年,第145頁。
(30)參看春醪:《梅訊(四十二)》,《申報》,1920年5月26日;佚名:《戲劇新聞.梅蘭芳來滬記》,《戲雜志》,第3號,1922年。
來源: 社科院網(wǎng)站
相關(guān)標簽:
濟南慶典公司
農(nóng)新
云上演出
戲曲
觀眾
名家
過年
記者
湖北
日報
相關(guān)新聞
- 2024-05-11北京演藝集團第十屆“五月演出季”如約
- 2024-05-11臨夏州赴天水市開展文藝演出暨文旅推介
- 2024-04-18淄博大劇院五周年重磅演出揭幕
- 2024-04-182024中國(天津)演出交易會開幕
服務范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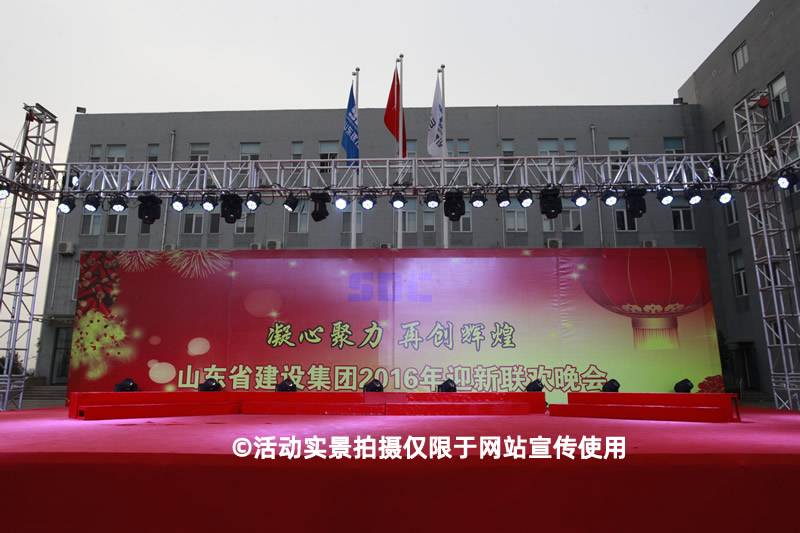


 客服
客服